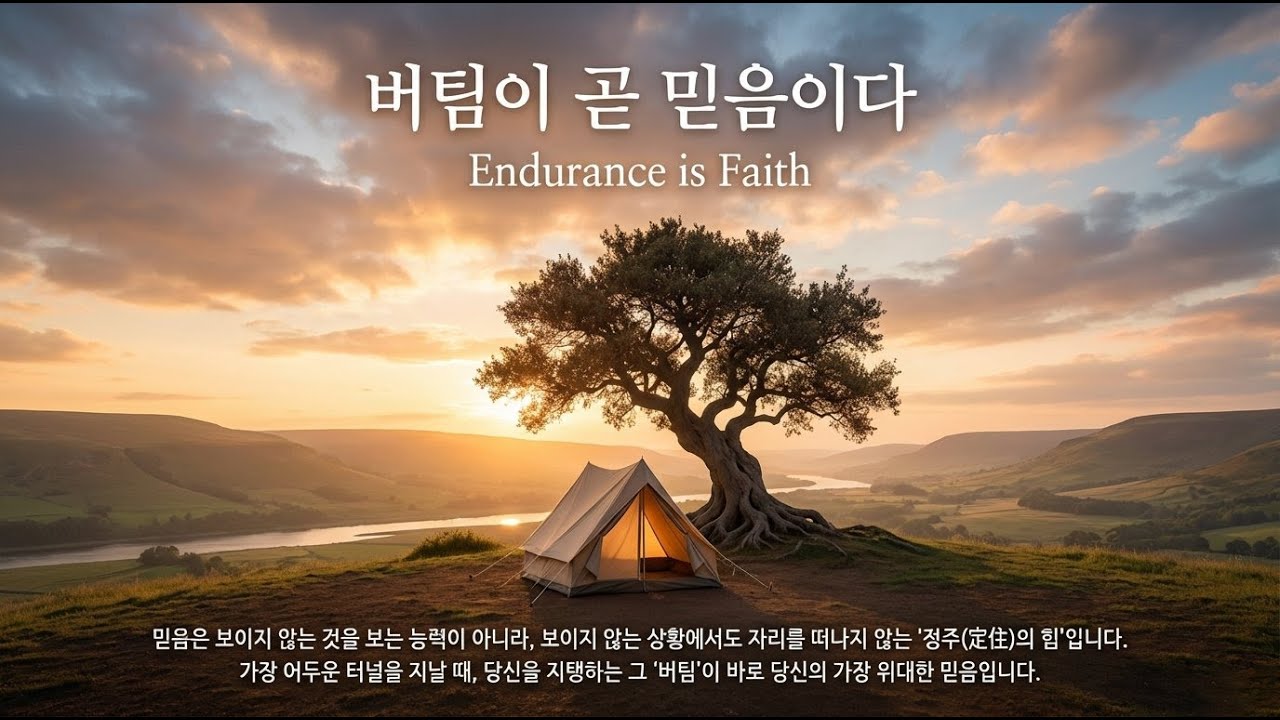д»Ҙ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зҡ„и®ІйҒ“дҝЎжҒҜдёәеҹәзЎҖпјҢе°Ҷ马еҸҜзҰҸйҹі14з« 32-42иҠӮвҖңе®ўиҘҝ马尼зҡ„зҘ·е‘ҠвҖқйҮҚж–°иҜ йҮҠдёәеӣӣж—¬жңҹй»ҳжғіпјҢж·ұе…Ҙз…§дә®вҖңйҳҝзҲёзҲ¶вҖқзҡ„дҝЎйқ гҖҒвҖңе„ҶйҶ’зҘ·е‘ҠвҖқзҡ„й—Ёеҫ’е‘јеҸ¬пјҢд»ҘеҸҠеҚҒеӯ—жһ¶йҒ“и·ҜдёҠзҡ„еӯӨзӢ¬дёҺеҗҢеңЁгҖӮ
еӣӣж—¬жңҹзҡ„з©әж°”жҖ»жҳҜжІүйҮҚгҖӮж—ҘеҺҶдёҠзңӢеҲ°вҖңеҸ—йҡҫе‘ЁвҖқдёүдёӘеӯ—зҡ„йӮЈдёҖеҲ»пјҢжҲ‘们зҡ„дҝЎд»°е°ұдјҡеҶҚж¬Ўиў«йӮҖиҜ·иө°еҗ‘жӣҙж·ұеӨ„гҖӮеј еӨ§еҚ«пјҲOlivet
University еҲӣеҠһдәәпјүзү§еёҲд№ӢжүҖд»ҘиҜ•еӣҫд»ҘвҖңдёҺеҹәзқЈеҗҢиЎҢвҖқзҡ„жЎҶжһ¶йҮҚ新讲解马еҸҜзҰҸйҹі14з« 32-42иҠӮвҖ”вҖ”д№ҹе°ұжҳҜе®ўиҘҝ马尼зҡ„зҘ·е‘ҠвҖ”вҖ”жӯЈеӣ дёәд»–жҠ“дҪҸдәҶиҝҷд»ҪйӮҖиҜ·зҡ„жң¬иҙЁгҖӮе®ўиҘҝ马尼并дёҚеҸӘжҳҜиҖ¶зЁЈжңҖеҗҺдёҖеӨңзҡ„жӮІеү§иҲһеҸ°пјҢе®ғжӣҙеғҸдёҖеҸ°вҖңзҒөйӯӮзҡ„еҺӢжҰЁжңәвҖқпјҡдҝЎеҝғйқ д»Җд№Ҳж’‘дҪҸпјҢйЎәжңҚз”Ёд»Җд№ҲиҜӯиЁҖе®ҢжҲҗпјҢд»ҘеҸҠй—Ёеҫ’зңҹе®һзҡ„иҪҜејұ究з«ҹжңүеӨҡиөӨиЈёпјҢйғҪеңЁеҗҢдёҖеӨ„иў«жҸӯејҖгҖӮ
дёҖдёӘиҖҗдәәеҜ»е‘ізҡ„еҲҮе…ҘзӮ№жқҘиҮӘзәҰзҝ°зҰҸйҹігҖӮеҜ№и§ӮзҰҸйҹід№ҰпјҲ马еӨӘгҖҒ马еҸҜгҖҒи·ҜеҠ пјүе…ұеҗҢдҝқз•ҷдёӢжқҘзҡ„е®ўиҘҝ马尼зҘ·е‘ҠпјҢеңЁзәҰзҝ°зҰҸйҹійҮҢеҚҙ并жңӘд»ҘеҸҷдәӢеҪўејҸеҮәзҺ°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и®ӨдёәпјҢиҝҷ并йқһз®ҖеҚ•зҡ„йҒ—жјҸпјҢиҖҢеҸҜи§ҶдёәзәҰзҝ°зңӢеҫ…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з„ҰзӮ№е·®ејӮгҖӮзәҰзҝ°зҰҸйҹіиҜҰе°Ҫ收еҪ•дәҶжңҖеҗҺжҷҡйӨҗеҗҺиҖ¶зЁЈжј«й•ҝзҡ„е‘ҠеҲ«и®Іи®әдёҺд»ЈзҘ·пјҲзәҰ13вҖ”17з« пјүпјҢйҡҸеҗҺдҫҝзӣҙжҺҘиҝӣе…Ҙиў«жҚ•еңәжҷҜпјҢжҠҠиҖ¶зЁЈзҡ„дё»еҠЁдёҺеҗӣзҺӢиҲ¬зҡ„еЁҒдёҘзҪ®дәҺеүҚеҸ°гҖӮеңЁиҝҷж ·зҡ„жҺЁиҝӣйҮҢпјҢиҖ¶зЁЈе№¶йқһжІЎжңүеҶ…еңЁжҢЈжүҺпјӣеҸӘжҳҜзәҰзҝ°жІЎжңүз”ЁеҸҷдәӢеҺ»йҮҚеӨҚвҖң第дёүж¬Ўзҡ„ж‘”и·ӨвҖқпјҢиҖҢжҳҜд»ҘвҖңжҲ‘еҝғйҮҢеҝ§ж„ҒвҖҰвҖҰжҲ‘еҸҜиҜҙпјҡзҲ¶е•ҠпјҢж•‘жҲ‘и„ұзҰ»иҝҷж—¶еҖҷеҗ—пјҹдҪҶжҲ‘еҺҹжҳҜдёәиҝҷж—¶еҖҷжқҘзҡ„вҖқпјҲзәҰ12:27пјүиҝҷж ·зҡ„йҷҲиҝ°пјҢжҠҠеҚҒеӯ—жһ¶д№ӢеүҚзҡ„ж‘Үж’јдёҺеҶіж–ӯд»ҘеҸҰдёҖз§Қж–№ејҸеҺӢзј©е‘ҲзҺ°гҖӮ
然иҖҢпјҢ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д»Қжү§ж„ҸжҠҠжҲ‘们еёҰеӣһ马еҸҜзҰҸйҹізҡ„е®ўиҘҝ马尼пјҢе…¶еҺҹеӣ 并дёҚйҡҫжҮӮпјҡд»–иҰҒжҲ‘们зңӢи§ҒпјҢйӮЈдҪҚвҖңе·Із»Ҹз«Ӣе®ҡеҝғеҝ—вҖқиө°еҗ‘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дё»пјҢ并дёҚжҳҜеғҸжІЎжңүжғ…з»ӘгҖҒжІЎжңүз—ӣи§үзҡ„и¶…и¶ҠжңәеҷЁдёҖж ·еүҚиЎҢпјӣзҲұ并йқһд»…йқ ж„Ҹеҝ—з»ҙжҢҒпјҢе®ғеҝ…йЎ»з©ҝи¶ҠзңјжіӘдёҺе‘је–ҠгҖӮе®ўиҘҝ马尼д»ҘжңҖе…·дәәжҖ§гҖҒжңҖжңүжё©еәҰзҡ„иүІеҪ©дёәжӯӨдҪңиҜҒгҖӮжҲ‘们еңЁиҝҷйҮҢйҒҮи§Ғзҡ„иҖ¶зЁЈжҳҜвҖңз”ҡжҳҜжғҠжҒҗпјҢжһҒе…¶йҡҫиҝҮвҖқгҖӮиҝҷеҸҘиҜқжҺҖејҖдәҶдҝЎд»°еёёжғійҒ®жҺ©зҡ„зңҹзӣёпјҡдҝЎеҝғдёҚжҳҜй’ўй“ҒиҲ¬зҡ„ж— иЎЁжғ…пјҢиҖҢжҳҜжҖҖзқҖйўӨжҠ–д»ҚдёҚйҖғи·‘зҡ„йҖүжӢ©пјӣиҖҢиҝҷз§ҚйҖүжӢ©пјҢеҸӘиғҪд»ҘвҖңзҘ·е‘ҠвҖқзҡ„еҪўжҖҒжҢҒз»ӯгҖӮ
вҖңе®ўиҘҝ马尼вҖқиҝҷдёӘеҗҚеӯ—жң¬иә«е°ұеёҰзқҖиұЎеҫҒж„Ҹе‘ігҖӮгҖҠеӨ§иӢұзҷҫ科全д№ҰгҖӢи§ЈйҮҠе®ғзҡ„еҗ«д№үдёәвҖңжҰЁжІ№еқҠ/жҰЁжІ№д№ӢеӨ„вҖқпјҲoil pressesпјүгҖӮж©„жҰ„иҰҒжҲҗдёәжІ№пјҢеҝ…йЎ»з»ҸеҺҶеҺӢеҠӣгҖӮжһңе®һеҺҹж ·д№ҹеҸҜиҠ¬иҠіпјҢдҪҶйӮЈиғҪй•ҝжңҹжүҝиҪҪйҰҷж°”дёҺе…үжіҪзҡ„жІ№пјҢеҚҙжҳҜд»ҺеҺӢжҰЁзҡ„ж—¶еҲ»жөҒеҮә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д№ӢжүҖд»Ҙд№…д№…еҒңз•ҷеңЁвҖңжҰЁжІ№еқҠвҖқзҡ„иҜ‘жі•дёҠпјҢд№ҹжӯЈеӣ дёәжӯӨпјҡе®ўиҘҝ马尼дёҚжҳҜиҖ¶зЁЈеҸ—иҶҸеҠ еҶ•гҖҒж¬ўе‘јзҷ»еңә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иҖҢжҳҜеҗӣзҺӢзҡ„жқғжҹ„еңЁ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йЎәжңҚдёӯиў«еҮҖзӮјд№ӢеӨ„пјӣзҲұзҡ„иҶҸжІ№еңЁиӢҰйҡҫзҡ„жҢӨеҺӢйҮҢиў«жҰЁеҮәд№ӢеӨ„гҖӮ
жӣҙдҪ•еҶөпјҢйӮЈдёҖеӨңиҝҳжҳҜйҖҫи¶ҠиҠӮд№ӢеӨңгҖӮеҪ“иҖ¶зЁЈе’Ңй—Ёеҫ’зҰ»ејҖжңүеңЈж®ҝзҡ„й«ҳеӨ„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пјҢи¶ҠиҝҮжұІжІҰи°·пјҢиө°еҗ‘ж©„жҰ„еұұж—¶пјҢ他们и„ҡдёӢд»ҝдҪӣжөҒж·ҢзқҖзҢ®зҘӯзҡ„еҺҶеҸІгҖҒиөҺзҪӘ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иў«жҺіеҲ°зҪ—马зҡ„зҠ№еӨӘеҸІе®¶зәҰз‘ҹеӨ«жӣҫи®°еҪ•йҖҫи¶ҠиҠӮзҢ®зҘӯзҡ„ж•°йҮҸпјҢиҜҙдёҖе№ҙйҖҫи¶ҠиҠӮжӣҫжңүвҖң256,500вҖқеҸӘзҘӯзүІпјҢ并жҸҗеҲ°дёҖеҸӘзҘӯзүІиҮіе°‘еҚҒдәәеҸӮдёҺпјҢеӣ жӯӨжҜҸйҖўиҠӮжңҹпјҢ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°ұдјҡиў«е·ЁеӨ§дәәжҪ®жҢӨж»ЎгҖӮеҚідҫҝе…ідәҺж•°еӯ—зІҫзЎ®жҖ§д»Қжңүдәүи®®пјҢиҝҷж®өи®°иҪҪиҮіе°‘и®©жҲ‘们зңӢи§ҒпјҡеҪ“ж—¶зҡ„иҖ¶и·Ҝж’’еҶ·еңЁйҖҫи¶ҠиҠӮжңҹй—ҙзЎ®е®һжҳҜдёҖеә§иў«вҖңиЎҖгҖҒзҫӨдј—дёҺзҙ§еј вҖқж’‘еӨ§зҡ„еҹҺеёӮгҖӮиҖ¶зЁЈзҡ„еҚҒеӯ—жһ¶дёҚжҳҜжҠҪиұЎж•ҷд№ү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зү№е®ҡиҠӮжңҹгҖҒзү№е®ҡж”ҝжІ»жҒҗжғ§гҖҒзү№е®ҡе®—ж•ҷзғӯеәҰзҡ„дёӯеҝғеҸ‘з”ҹзҡ„еҺҶеҸІдәӢ件гҖӮ
然иҖҢй—Ёеҫ’еҚҙд»ҘжӯҢеЈ°з©ҝиҝҮйӮЈдёҖеӨңгҖӮвҖң他们е”ұдәҶиҜ—пјҢе°ұеҮәжқҘеҫҖж©„жҰ„еұұеҺ»вҖқпјҲеҸӮеҸҜ14пјүиҝҷеҸҘеҸҷиҝ°е№ійқҷеҫ—иҝ‘д№ҺдёҚзҘҘ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еңЁиҝҷйҮҢжҚ•жҚүеҲ°й—Ёеҫ’зҡ„вҖңеӨұеҺ»ж„ҹзҹҘвҖқпјҡдё»зҡ„еҝғйҮҢе·Із»Ҹжё…жҘҡжө®зҺ°иғҢеҸӣзҡ„еҫҒе…ҶдёҺжӯ»дәЎзҡ„йҳҙеҪұпјҢй—Ёеҫ’еҚҙиҜ»дёҚеҮәж°ӣеӣҙпјҢжҠҠиөһзҫҺеҪ“дҪңдҪ“йқўпјҢ然еҗҺеҫҲеҝ«е°ұеҮҶеӨҮзқЎеҺ»гҖӮеҜ№жҜ”并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еҚ•зәҜиҙЈеӨҮй—Ёеҫ’пјҢиҖҢеғҸдёҖйқўй•ңеӯҗз…§еҗ‘жҲ‘们пјҡжҲ‘们常жҠҠвҖңе”ұиҜ—вҖқзӣҙжҺҘзӯүеҗҢдәҺ敬иҷ”пјҢеҚҙеҝҳдәҶе®ғд№ҹеҸҜиғҪжҲҗдәҶйҖғйҒҝзҺ°е®һ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ӮжүҝеҸ—дёҚдәҶйҮҚйҮҸзҡ„зҒөйӯӮпјҢеёёз”ЁжӯҢеЈ°йҒ®зӣ–гҖӮе®ўиҘҝ马尼撕ејҖйӮЈеұӮжӯҢеЈ°пјҢи®©жҲ‘们зңӢи§ҒиөӨиЈёгҖҒиҝ‘д№ҺвҖңиЈёйңІзҡ„вҖқдҝЎд»°зңҹе®һгҖӮ
иҖ¶зЁЈеңЁеҚҒдёҖдёӘй—Ёеҫ’дёӯеҸҲеёҰдәҶдёүдёӘдәәвҖ”вҖ”еҪјеҫ—гҖҒйӣ…еҗ„гҖҒзәҰзҝ°вҖ”вҖ”иҝӣе…Ҙжӣҙж·ұеӨ„гҖӮиҝҷзңӢдјјзү№жқғпјҢе…¶е®һжҳҜеҗҢиө°зҡ„иҜ·жұӮгҖӮвҖңдҪ 们иҰҒиӯҰйҶ’вҖқдёҚжҳҜдёҖеҸҘз®ҖеҚ•зҡ„зІҫзҘһеҸЈеҸ·пјҢиҖҢжҳҜзҲұзҡ„жңҖеҗҺжҒіжұӮгҖӮжҒіжұӮеҙ©еЎҢзҡ„зһ¬й—ҙпјҢеҚҒеӯ—жһ¶йҒ“и·Ҝзҡ„еӯӨзӢ¬е°ұжӣҙжё…жҷ°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дёҚж–ӯејәи°ғзҡ„вҖңеҹәзқЈзҡ„еӯӨзӢ¬вҖқжӯЈд»ҺжӯӨеӨ„жҲҗз«Ӣпјҡдё»иғҢиҙҹзҡ„жҳҜй—Ёеҫ’ж— жі•д»Јжүӣзҡ„йҮҚжӢ…пјҢдҪҶиҮіе°‘зӣјжңӣ他们иғҪйҷӘзқҖйҶ’зқҖгҖӮ然иҖҢ他们зқЎдәҶгҖӮвҖңеҝғзҒөеӣә然ж„ҝж„ҸпјҢиӮүдҪ“еҚҙиҪҜејұдәҶвҖқз”ЁдёҖеҸҘиҜқи§Јеү–дәҶдәәзҡ„з»“жһ„пјҡж„Ҹеҝ—зҹҘйҒ“ж–№еҗ‘пјҢдҪҶд№ жғҜгҖҒз–Іжғ«дёҺжғ§жҖ•и®©иә«дҪ“иәәдёӢгҖӮжүҖд»ҘдҝЎд»°жӣҙеғҸвҖңи®ӯз»ғвҖқиҖҢйқһвҖңе®ЈиӘ“вҖқпјӣиҖҢи®ӯз»ғзҡ„дёӯеҝғпјҢе°ұжҳҜиғңиҝҮзқЎж„Ҹзҡ„зҘ·е‘ҠгҖӮ
е®ўиҘҝ马尼зҘ·е‘Ҡзҡ„й«ҳеі°пјҢд»ҺиҖ¶зЁЈзҡ„з§°е‘јејҖе§ӢпјҡвҖңйҳҝзҲёпјҢзҲ¶е•ҠгҖӮвҖқ вҖңйҳҝзҲёвҖқжҳҜиҖ¶зЁЈжүҖз”Ёзҡ„дәҡе…°иҜӯиЎЁиҫҫпјӣдҝқзҪ—д№ҹиҜҙжҲ‘们еңЁеңЈзҒөйҮҢиғҪеҰӮжӯӨе‘јеҸ«зҘһгҖӮеҸӘжҳҜпјҢжҠҠвҖңйҳҝзҲёвҖқдёҖжҰӮзҝ»жҲҗиҪ»жқҫеҸЈиҜӯйҮҢзҡ„вҖңзҲёзҲё/зҲ№ең°вҖқпјҢд№ҹйңҖиҰҒи°Ёж…Һпјҡе®ғзЎ®е®һеҢ…еҗ«дәІеҜҶпјҢеҚҙдёҚжҳҜиҪ»жө®зҡ„дәІиҝ‘пјҢиҖҢжҳҜ敬з•Ҹдёӯзҡ„дәІиҝ‘гҖҒе°ҠиҚЈдёӯзҡ„йқ иҝ‘вҖ”вҖ”и®ёеӨҡзҘһеӯҰ家йғҪејәи°ғиҝҷдёҖеұӮ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Ҡ“дҪҸзҡ„д№ҹжӯЈжҳҜиҝҷз§ҚиҙЁең°пјҡеңЁеҚҒеӯ—жһ¶йқўеүҚпјҢиҖ¶зЁЈдёҚжҳҜжҠҠзҘһеҪ“дҪңйҷҢз”ҹзҡ„е®ЎеҲӨиҖ…е‘је–ҠпјҢиҖҢжҳҜз§°зҘӮдёәвҖңжҲ‘зҡ„зҲ¶вҖқгҖӮиҝҷдёҖдёӘз§°е‘јпјҢжҲҗдёәдҝЎд»°жңҖеҗҺзҡ„ж”Ҝж’‘зӮ№пјӣеӣ дёәдёҖж—ҰеҜ№зҲ¶зҡ„зҲұеӨұеҺ»жҠҠжҸЎпјҢйЎәжңҚе°ұдјҡиҝ…йҖҹеҸҳиҙЁдёәз»қжңӣгҖӮ
дҪҶиҝҷз§ҚжҠҠжҸЎе№¶дёҚдјҡжҠ№йҷӨжғ…з»ӘгҖӮиҖ¶зЁЈзҘҲжұӮпјҡвҖңжұӮдҪ е°ҶиҝҷжқҜж’ӨеҺ»гҖӮвҖқиҝҷдёҚжҳҜйҖғйҒҝзҡ„зҪӘпјҢиҖҢжҳҜдәәжҖ§зҡ„иҜҡе®һ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д№ӢжүҖд»ҘжҠҠиҝҷдёҖж®өиҜ»жҲҗвҖңе®үж…°вҖқ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®ғиҜҒжҳҺпјҡдҝЎеҫ’зҡ„жғ§жҖ•дёҺжҲҳж —дёҚеҝ…然зӯүеҗҢдәҺдёҚдҝЎгҖӮе…ій”®дёҚеңЁдәҺвҖңжңүжІЎжңүжғ§жҖ•вҖқпјҢиҖҢеңЁдәҺвҖңжҠҠжғ§жҖ•еёҰеҲ°и°ҒйқўеүҚвҖқгҖӮиҖ¶зЁЈе№¶дёҚеҗ‘дәәеӨёеј иҜүиӢҰпјҢиҖҢжҳҜеҗ‘зҲ¶еҖҫиҜүпјӣ并且з«ӢеҲ»иҪ¬еҗ‘зҘ·е‘Ҡзҡ„ж–№еҗ‘пјҡвҖң然иҖҢдёҚиҰҒд»ҺжҲ‘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еҸӘиҰҒд»ҺдҪ зҡ„ж„ҸжҖқгҖӮвҖқиҝҷдёҚжҳҜи®Өе‘ҪпјҢиҖҢжҳҜд»ҘдҝЎйқ дёәж №еҹәзҡ„иҮӘжҲ‘дәӨжүҳгҖӮеҹәзқЈж•ҷзҡ„йЎәжңҚдёҚжҳҜжғ…з»Әзҡ„зјәеёӯпјҢиҖҢжҳҜи¶…и¶Ҡжғ…з»ӘгҖҒеҹәдәҺе…ізі»зҡ„йҖүжӢ©гҖӮ
зҗҶи§ЈиҝҷйЎәжңҚпјҢд№ҹиҰҒеҝҶиө·ж—§зәҰзҡ„йў„иЁҖиғҢжҷҜгҖӮиҖ¶зЁЈеҜ№й—Ёеҫ’еј•з”ЁвҖңжҲ‘иҰҒеҮ»жү“зү§дәәпјҢзҫҠе°ұеҲҶж•ЈдәҶвҖқпјҲи§ҒеҸҜ14пјүпјҢжҠҠж’’иҝҰеҲ©дәҡд№Ұ13з« 7иҠӮзҡ„йў„иЁҖеҸ еҠ еңЁиҮӘе·ұзҡ„йҒ“и·ҜдёҠпјҡвҖңеҮ»жү“зү§дәәпјҢзҫҠе°ұеҲҶж•ЈгҖӮвҖқеҚҒеӯ—жһ¶дёҚжҳҜеҒ¶еҸ‘дәӢж•…пјҢиҖҢжҳҜзҘӮвҖңжҳҺзҹҘвҖқд»Қиҝӣе…Ҙзҡ„и·ҜгҖӮеҚідҫҝеҰӮжӯӨпјҢеңЁе®ўиҘҝ马尼пјҢиҖ¶зЁЈд»Қд»ҘзҘ·е‘ҠеҶҚдёҖж¬ЎвҖңиӘҠеҶҷвҖқйӮЈжқЎи·Ҝпјҡйў„е®ҡдёҺйЎәжңҚеңЁжӯӨзҙ§зҙ§жүЈеҗҲгҖӮзҹҘйҒ“зҲ¶зҡ„ж—Ёж„ҸиүҜе–„пјҢ并дёҚзӯүдәҺйӮЈжқЎи·Ҝзҡ„иӢҰ涩дјҡж¶ҲеӨұпјӣиҖҢжҳҜйӮЈиӢҰ涩иҺ·еҫ—ж„Ҹд№үгҖӮе®ўиҘҝ马尼зҡ„йЎәжңҚдёҚжҳҜвҖңжІЎеҠһжі•вҖқпјҢиҖҢжҳҜвҖңеӣ дҪ иүҜе–„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дҝЎиҖҢиЎҢвҖқгҖӮ
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и§ЈиҜ»зҡ„еҸҰдёҖдёӘејәеӨ„пјҢжҳҜд»–дёҚжҠҠиҝҷж®өз»Ҹж–ҮеҸӘеҪ“дҪңвҖңзҘһеӯҰж ҮеҮҶзӯ”жЎҲвҖқпјҢиҖҢжҳҜжҠҠе®ғжӢүеӣһвҖңдәәзҡ„зңҹе®һвҖқгҖӮжҲ‘们常и°ҲиҖ¶зЁЈзҡ„йЎәжңҚпјҢеҚҙдёҚж„ҝжғіиұЎйӮЈйЎәжңҚдјҙйҡҸжҖҺж ·зҡ„еҝғзҗҶйҮҚйҮҸпјҢд»ҘеҸҠйӮЈйҮҚйҮҸеҰӮдҪ•еңЁиә«дҪ“еҸҚеә”йҮҢж¶ҢеҮәвҖ”вҖ”жұ—гҖҒе‘јеҗёгҖҒеҝғи·ігҖҒеҸ‘жҠ–гҖӮдҪҶзҰҸйҹід№ҰеҲ»ж„Ҹи®°еҪ•вҖңжғҠжҒҗвҖқдёҺвҖңеҝ§дјӨвҖқпјҢжӯЈж„Ҹе‘ізқҖпјҡдёҠеёқжІЎжңүжҠҠдәәзҡ„и„Ҷејұй©ұйҖҗеҲ°дҝЎд»°д№ӢеӨ–гҖӮеҪ“ж•ҷдјҡеҸӘеұ•зӨәзңӢиө·жқҘејәеЈ®зҡ„дҝЎеҝғж—¶пјҢеҸ—дјӨзҡ„дәәе°ұдјҡжҠҠиҮӘе·ұзҡ„жғ…з»ӘеҗһжҲҗзҪӘз–ҡгҖӮе®ўиҘҝ马尼зә жӯЈиҝҷз§ҚжүӯжӣІпјҡжүҝи®ӨвҖңжҲ‘е®іжҖ•вҖқпјҢдёҚдёҖе®ҡжҳҜдҝЎеҝғеҙ©жәғпјҢеҸҚиҖҢеҸҜиғҪжҳҜдҝЎеҝғд»ҘзҘ·е‘Ҡзҡ„ж–№ејҸиҜҡе®һжҳҫеҪўзҡ„第дёҖжӯҘгҖӮ
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вҖңжқҜвҖқзҡ„ж„ҸиұЎд№ҹеҸҳеҫ—жӣҙдё°еҺҡгҖӮеңЈз»ҸдёӯжқҜжңүж—¶иұЎеҫҒе®ЎеҲӨдёҺйңҮжҖ’пјҢжңүж—¶иұЎеҫҒиӢҰйҡҫзҡ„д»ҪгҖӮиҖ¶зЁЈжүҖиҜҙвҖңиҝҷжқҜвҖқпјҢдёҚд»…жҳҜиӮүдҪ“з–јз—ӣпјҢд№ҹеҢ…еҗ«зҪӘдәәд№ӢжүӢдәӨд»ҳеёҰжқҘзҡ„зҫһиҫұгҖҒеҶӨеұҲгҖҒе…ізі»зҡ„иғҢеҸӣпјҢд»ҘеҸҠдёҺзҘһж–ӯиЈӮиҲ¬зҡ„вҖңиў«ејғз»қвҖқж·ұжёҠгҖӮеӣ жӯӨиҖ¶зЁЈзҡ„зҘ·е‘ҠдёҚд»…жҳҜжғійҒҝејҖз—ӣзҡ„жң¬иғҪпјҢжӣҙжҳҜз«ҷеңЁеӯҳеңЁе°Ҷиў«ж’•иЈӮзҡ„жӮ¬еҙ–иҫ№зјҳзҡ„е‘је–ҠгҖӮиҖҢеҶіе®ҡжҖ§д№ӢеӨ„еңЁдәҺпјҡйӮЈе‘је–Ҡд»ҚдёҚжқҫејҖвҖңйҳҝзҲёвҖқзҡ„з§°е‘јгҖӮжғ…з»Әзҝ»ж¶ҢпјҢе…ізі»еҚҙдёҚж–ӯиЈӮгҖӮжӯЈеҰ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үҖејәи°ғпјҢдҝЎд»°зҡ„еҚұжңәз»Ҳ究еҸ‘з”ҹеңЁвҖңеҜ№зҲ¶д№ӢзҲұзҡ„зЎ®дҝЎвҖқж‘ҮеҠЁд№Ӣж—¶пјҡдёҖж—ҰжҖҖз–‘зҲұпјҢйЎәжңҚе°ұжҲҗдәҶд№үеҠЎпјҢд№үеҠЎеёҰжқҘиҖ—з«ӯпјӣзӣёеҸҚпјҢдёҖж—ҰдҝЎд»»зҲұпјҢйЎәжңҚеҚідҪҝеңЁз—ӣдёӯд№ҹд»ҚжҳҜжңүж„Ҹд№үзҡ„йҖүжӢ©гҖӮ
й—Ёеҫ’зҡ„зқЎзң еҲҷеұ•зӨәдәҶиҝҷйҖүжӢ©зҡ„еҸҚйқўгҖӮеҪјеҫ—еңЁеүҚдёҖеҲ»иҝҳиҜҙвҖңжҲ‘е°ұжҳҜеҝ…йЎ»е’ҢдҪ еҗҢжӯ»пјҢд№ҹжҖ»дёҚиғҪдёҚи®ӨдҪ вҖқпјҢеҸҜдёҚд№…еҗҺд»–иҝһдёҖдёӘж—¶иҫ°йғҪдёҚиғҪйҶ’зқҖгҖӮиҝҷз§ҚеҸҚеӨҚ并йқһеҪјеҫ—зӢ¬жңүгҖӮдәәеҫҖеҫҖеңЁз«Ӣеҝ—ж—¶й«ҳдј°иҮӘе·ұпјҢеңЁжүҝеҸ—ж—¶дҪҺдј°иҮӘе·ұпјҡиӘ“иЁҖе®ҸеӨ§пјҢеҝҚиҖҗзҡ„жҠҖжңҜеҚҙиҙ«зҳ гҖӮдәҺжҳҜиҖ¶зЁЈеҗ©е’җпјҡвҖңжҖ»иҰҒиӯҰйҶ’зҘ·е‘ҠпјҢе…Қеҫ—е…ҘдәҶиҝ·жғ‘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зҡ„вҖңиҜ•жҺў/иҝ·жғ‘вҖқдёҚд»…жҳҜйҒ“еҫ·иҜұжғ‘пјҢд№ҹеҢ…жӢ¬дҪҝдәәж”ҫејғе…ізі»зҡ„з–Іжғ«гҖҒдҪҝдәәйҖғйҒҝиҙЈд»»зҡ„жҒҗжғ§гҖҒдҪҝдәәжҠҠдҝЎеҝғвҖңжҺЁеҲ°д»ҘеҗҺвҖқзҡ„йә»жңЁгҖӮиӯҰйҶ’дёҚжҳҜзІҫзҘһиғңеҲ©жҲ–жғ…з»ӘдәўеҘӢ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еҝғиҰҒеҸҳй’қд№ӢеүҚпјҢжҠҠе®ғдёҖж¬Ўж¬ЎиҪ¬еҗ‘зҘһзҡ„еҫ®е°ҸйҮҚеӨҚгҖӮ
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еҖҹжӯӨжҸҗйҶ’жҲ‘们пјҡвҖңдёҺеҹәзқЈеҗҢиЎҢвҖқз»Ҳ究ж„Ҹе‘ізқҖвҖңдёҺзҘӮдёҖеҗҢиӯҰйҶ’вҖқгҖӮеҗҢиЎҢдёҚжҳҜеҗҢеӨ„дёҖдёӘз©әй—ҙпјҢиҖҢжҳҜеҲҶжӢ…еҗҢдёҖд»Ҫе…іеҲҮдёҺйҮҚйҮҸгҖӮйӮЈдёҖеӨ©й—Ёеҫ’зЎ®е®һеңЁеҗҢдёҖеә§еӣӯеӯҗйҮҢ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жҙ»еңЁеҗҢдёҖдёӘеӨңйҮҢпјҡиҖ¶зЁЈзҡ„еӨңжҳҜзҘ·е‘Ҡзҡ„еӨңпјҢй—Ёеҫ’зҡ„еӨңжҳҜзқЎзң зҡ„еӨңпјӣиҖҢиҝҷйҒ“зјқйҡҷдҪҝиҖ¶зЁЈжӣҙеӯӨеҚ•гҖӮжҲ‘们д№ҹеёёеҰӮжӯӨпјҡеҚідҫҝеқҗеңЁзӨјжӢңе ӮпјҢеҚідҫҝз«ҷеңЁеҲ«дәәзҡ„з—ӣиӢҰйқўеүҚпјҢжҲ‘们д»ҚеҸҜиғҪд»ҘвҖңзқЎзқҖзҡ„еҝғвҖқеҮәзҺ°вҖ”вҖ”жіЁж„ҸеҠӣеңЁеҲ«еӨ„пјҢзҲұе·Із–Іжғ«пјҢиҙЈд»»д»ӨдәәеҺҢзғҰгҖӮе®ўиҘҝ马尼ж‘ҮйҶ’иҝҷж ·зҡ„еҝғгҖӮвҖңдҪ 们еңЁиҝҷйҮҢзӯүеҖҷпјҢиӯҰйҶ’вҖқд№ҹ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иҜҒжҚ®пјҡеҹәзқЈеңЁз—ӣиӢҰд№ӢеӨңд»ҚдёҚж”ҫејғзҫӨдҪ“пјҢзӣҙеҲ°жңҖеҗҺдёҖеҲ»д»ҚеңЁиҜ·жұӮвҖңжҲ‘们дёҖиө·вҖқгҖӮ
然иҖҢзҰҸйҹід№ҰеҶ·йқҷзҡ„иҜҡе®һ并дёҚжҺ©йҘ°пјҡиҝҷиҜ·жұӮиў«жӢ’з»қдәҶ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и°ҲвҖңеӯӨзӢ¬вҖқдёҚжҳҜжғ…з»ӘеҢ–дҝ®иҫһпјҢиҖҢжҳҜж•‘иөҺеҸІзҡ„дәӢе®һпјҡж— дәәиғҪд»Јжӣҝзҡ„йЎәжңҚз”ұиҖ¶зЁЈзӢ¬иҮӘжүҝжӢ…пјҢиҝһжңҖдәІиҝ‘зҡ„й—Ёеҫ’д№ҹжІЎиғҪеҲҶжӢ…йӮЈйҮҚйҮҸгҖӮдәҺжҳҜжҲ‘们жӣҙжё…жҘҡиҜ»еҲ°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жҒ©е…ёпјҡеҚҒеӯ—жһ¶дёҚжҳҜжҲ‘们дёҖеҗҢжҠ¬иө·зҡ„еҠҹз»©пјҢиҖҢжҳҜжҲ‘们зқЎзқҖж—¶зҘӮзӢ¬иҮӘдёҫиө·зҡ„ж•‘жҒ©гҖӮеӣ жӯӨжҒ©е…ёе№¶дёҚе»үд»·пјӣзӣёеҸҚпјҢжҒ©е…ёеӣ жҳҜвҖңжҲ‘жңӘиғҪеҸӮдёҺзҡ„зҲұвҖқиҖҢжӣҙеҲәз—ӣгҖӮд№ҹжӯЈжҳҜиҝҷз§ҚеҲәз—ӣпјҢжҲҗдёәжҲ‘们йҮҚж–°йҶ’жқҘзҡ„еҠЁеҠӣгҖӮ
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ҠҠ马еҸҜзҰҸйҹійҮҢйӮЈдҪҚвҖңйқ’е№ҙдәәвҖқзҡ„ж•…дәӢеҠ иҝӣжқҘпјҢд№ҹжҳҜдёәдәҶи®©жҲ‘们зӣҙйқўиҝҷз§ҚвҖңжңӘиғҪеҸӮдёҺвҖқзҡ„зҫһ愧гҖӮдәәйҖҡеёёжғіи®°еҪ•иҮӘе·ұзҡ„иӢұйӣ„дәӢиҝ№пјҢдҪҶ马еҸҜзҰҸйҹійҮҢж„ҸеӨ–ең°еҮ д№ҺжІЎжңүиӢұйӣ„пјҡйҖғи·‘зҡ„й—Ёеҫ’гҖҒзқЎзқҖзҡ„жңӢеҸӢгҖҒжІүй»ҳзҡ„зҫӨдј—пјҢд»ҘеҸҠзӢ¬иҮӘзҘ·е‘Ҡзҡ„иҖ¶зЁЈвҖ”вҖ”д»…жӯӨиҖҢе·ІгҖӮжӯЈжҳҜиҝҷз§ҚеҸҷиҝ°ж–№еҗ‘пјҢдҪҝзҰҸйҹіжҳҫеҫ—зңҹе®һпјҡзҰҸйҹідёҚжҳҜдәәзұ»жҲҗе°ұпјҢиҖҢжҳҜдёҠеёқд»Ӣе…ҘгҖӮж•‘жҒ©дёҚжҳҜеӣ дёәжҲ‘们еҸҳеҫ—жӣҙеҘҪжүҚжқҘеҲ°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жҲ‘д»¬ж— еҠӣзҡ„ж—¶еҲ»пјҢзҲұд»ҚдёҚж”ҫејғпјҢжүҖд»Ҙж•‘жҒ©жқҘеҲ°гҖӮ
дҪҶиҝҷ并дёҚжҳҜз»ҷжҲ‘们дёҖеј вҖңеҸҚжӯЈжҲ‘们еҒҡдёҚеҲ°пјҢе°ұйҡҸдҫҝеҗ§вҖқзҡ„йҖҡиЎҢиҜҒпјҢжҒ°жҒ°зӣёеҸҚгҖӮзңҹжӯЈзңӢи§ҒиҖ¶зЁЈзҡ„еӯӨзӢ¬зҡ„дәәпјҢдјҡдёҚеҶҚж„ҝж„Ҹи®©дё»зӢ¬иҮӘеүҚиЎҢгҖӮ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ңҖеҗҺе‘јеҗҒвҖңеҰӮд»ҠиҜҘиҪ®еҲ°жҲ‘们еҗҢиЎҢвҖқпјҢжӯЈжҳҜеӣ дёәиҝҷйҮҢгҖӮдҝЎд»°еёёеёёжқҘеҫ—еӨӘжҷҡпјҡжҲ‘们жҖ»еңЁдәӢ件иҝҮеҺ»еҗҺжүҚзҹҘйҒ“ж„Ҹд№үгҖӮй—Ёеҫ’д№ҹжҳҜеңЁеӨҚжҙ»д№ӢеҗҺжүҚжӣҙжё…жҘҡжҳҺзҷҪиҖ¶зЁЈжҳҜи°ҒгҖҒйӮЈдёҖеӨңжҳҜд»Җд№ҲгҖӮ然иҖҢеӣӣж—¬жңҹйӮҖиҜ·жҲ‘们жҠҠвҖңеҗҺжӮ”зҡ„ж—¶й—ҙвҖқж”№жҲҗвҖңйў„йҳІзҡ„ж—¶й—ҙвҖқпјҡдёҚиҰҒеҸӘеңЁдәӢеҗҺжөҒжіӘпјҢиҖҢиҰҒд»ҘеҪ“дёӢзҡ„иӯҰйҶ’еӣһеә”дё»зҡ„йҒ“и·ҜгҖӮ
иҝҷз§Қеӣһеә”еҝ…йЎ»иў«зҝ»иҜ‘жҲҗж—ҘеёёиҜӯиЁҖгҖӮе®ўиҘҝ马尼зҡ„зҘ·е‘ҠдёҚиғҪеҸӘеҒңз•ҷеңЁеңЈең°зҡ„ж„ҹеҠЁйҮҢгҖӮвҖңдёҚиҰҒз…§жҲ‘зҡ„ж„ҸжҖқвҖқиҰҒиҗҪиҝӣдјҡи®®е®Өзҡ„йҖүжӢ©гҖҒ家еәӯйҮҢзҡ„еҶІзӘҒгҖҒйҮ‘й’ұдёҺж—¶й—ҙзҡ„дҪҝз”ЁгҖҒе…ізі»дёӯзҡ„иҜҡе®һгҖҒйҘ¶жҒ•зҡ„еҶіе®ҡгҖӮж”ҫдёӢе·ұж„ҸдёҚжҳҜжҠ№йҷӨиҮӘжҲ‘пјҢиҖҢжҳҜжҠҠиҮӘе·ұе®үзҪ®еңЁжӣҙеӨ§зҡ„зҲұзҡ„秩еәҸдёӯпјӣиҝҷжҳҜдёҖйЎ№йқһеёёдё»еҠЁ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жңүдәӣж—ҘеӯҗпјҢвҖңжӯЈзЎ®зҡ„йҖүжӢ©вҖқзңӢиө·жқҘе°ұжҳҜвҖңеҗғдәҸвҖқпјҢвҖңжІүй»ҳвҖқеғҸжҳҜвҖңеӨұиҙҘвҖқпјҢвҖңйҘ¶жҒ•вҖқиў«иҜҜи§ЈдёәвҖңиҪҜејұвҖқгҖӮдҪҶеҹәзқЈиө°зҡ„жҳҜеңЁиҪҜејұдёӯжҳҫеҮәеҲҡејәзҡ„и·ҜпјӣдҝқзҪ—иғҪиҜҙвҖңжҲ‘д»Җд№Ҳж—¶еҖҷиҪҜејұпјҢд»Җд№Ҳж—¶еҖҷе°ұеҲҡејәдәҶвҖқпјҢд№ҹжҳҜеӣ дёәд»–еӯҰдјҡдәҶиҝҷжқЎи·Ҝзҡ„йҖ»иҫ‘гҖӮ
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зҡ„и®ІйҒ“йҮҢжңүдёҖз§ҚжҠ“дҪҸжӮ–и®әзҡ„зү§е…»и§Ұи§үпјҡд»–дёҚжҠҠдҝЎд»°еҢ…иЈ…жҲҗвҖңиғңеҲ©зҡ„зӨјзӣ’вҖқпјҢеҸҚеҖ’её®еҠ©жҲ‘们жүҝи®ӨиҮӘе·ұзҡ„жқҫж•ЈпјҢ并еӣ иҝҷжқҫж•ЈиҖҢжӣҙж·ұзҘ·е‘ҠгҖӮвҖңеҝғзҒөеӣә然ж„ҝж„ҸпјҢиӮүдҪ“еҚҙиҪҜејұвҖқдёҚжҳҜеӨұиҙҘе®ЈиЁҖпјҢиҖҢжҳҜзҘ·е‘Ҡзӯ–з•ҘпјҡиӢҘзҒөйӯӮзңҹзҡ„ж„ҝж„ҸпјҢе°ұиҰҒж•ҙзҗҶзҺҜеўғпјҢи®©иә«дҪ“и·ҹдёҠгҖӮзҶ¬еӨң并дёҚеҝ…然жӣҙ敬иҷ”пјӣдёәдәҶиҜҘеҒҡзҡ„дәӢж—©зқЎж—©иө·пјҢеҸҚиҖҢеҸҜиғҪжӣҙ敬иҷ”гҖӮиғңиҝҮжҖ’ж°”зҡ„еҠӣйҮҸдёҚжҳҜж„Ҹеҝ—зҡ„зҲҶзӮёпјҢиҖҢжҳҜжҖ’ж°”е–·ж¶Ңд№ӢеүҚе…ҲжҠҠеҝғеҖҫеҖ’еңЁзҘһйқўеүҚзҡ„д№ жғҜпјӣиғңиҝҮиҜұжғ‘д№ҹдёҚжҳҜжҹҗдёҖж¬ЎиӢұйӣ„ејҸеҶіж–ӯпјҢиҖҢжҳҜвҖңе…Қеҫ—е…ҘдәҶиҝ·жғ‘вҖқзҡ„жҸҗеүҚиӯҰйҶ’дёҺйҮҚеӨҚгҖӮ
жӯӨеӨ–пјҢе®ўиҘҝ马尼д№ҹеңЁиҝҪй—®зҫӨдҪ“зҡ„иҙЈд»»гҖӮжҲ‘们常еңЁеҲ«дәәеҙ©жәғж—¶й—®пјҡвҖңдҪ жҖҺд№Ҳиҝҷд№ҲиҪҜејұпјҹвҖқеҸҜзҰҸйҹід№Ұе…Ҳй—®зҡ„еҸҜиғҪжҳҜпјҡвҖңдҪ дёәд»Җд№ҲжІЎжңүйҷӘд»–дёҖиө·иӯҰйҶ’пјҹвҖқ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үҖиҜҙзҡ„еҗҢиЎҢпјҢжҳҜдёҖз§ҚеҪјжӯӨжүҝжӢ…зҡ„дҝЎд»°гҖӮеҪ“жҹҗдёӘдәәиҝӣе…ҘиҮӘе·ұзҡ„е®ўиҘҝ马尼д№ӢеӨңж—¶пјҢж—Ғиҫ№йӮЈдёҖзӮ№зӮ№е®ҲеҖҷвҖ”вҖ”йҷӘд»–еқҗзқҖгҖҒе“ӘжҖ•з®Җзҹӯдёәд»–зҘ·е‘ҠгҖҒз”ЁдёҖеҸҘе…ӢеҲ¶иҖҢз«ҜжӯЈзҡ„иҜқз•ҷеңЁйӮЈйҮҢвҖ”вҖ”йғҪеҸҜиғҪж•‘дәәгҖӮиҖ¶зЁЈжңҖз»Ҳд»ҚзӢ¬иҮӘиө°еҗ‘еҚҒеӯ—жһ¶пјҢдҪҶзҘӮзҡ„ж•ҷдјҡдёҚиҜҘеҶҚи®©дәәзӢ¬иҮӘжүҝеҸ—гҖӮд»ҠеӨ©еҪ“жҲ‘们еңЁеҪјжӯӨзҡ„е®ўиҘҝ马尼йҮҢдҝқжҢҒжё…йҶ’пјҢжҲ‘们е°ұ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иғҪзЁҚеҫ®еҮҸиҪ»еҚҒеӯ—жһ¶еӯӨзӢ¬зҡ„зҫӨдҪ“гҖӮ
еңЁиҝҷдёҖзӮ№дёҠпјҢиүәжңҜд№ҹдёәжҲ‘们жү“ејҖжӣҙж·ұзҡ„йҖҡйҒ“гҖӮж„ҸеӨ§еҲ©ж–ҮиүәеӨҚе…ҙ画家е®үеҫ·зғҲдәҡВ·жӣјзү№е°јдәҡзҡ„гҖҠThe Agony in
the GardenгҖӢпјҲзәҰ1455вҖ”1456пјүз”Ёд»–йӮЈз§ҚеқҡзЎ¬иҖҢеҶ·йқҷзҡ„笔и§ҰпјҢжҠҠе®ўиҘҝ马尼д№ӢеӨңи§Ҷи§үеҢ–пјҡз”»йқўдёӯеҹәзқЈзӢ¬иҮӘи·ӘеңЁеІ©зҹіиҲ¬зҡ„ең°еҪўдёҠпјҢиҝңеӨ„зҠ№еӨ§еёҰзқҖе…өдёҒйҖјиҝ‘пјҢдёӢж–№еҪјеҫ—гҖҒйӣ…еҗ„гҖҒзәҰзҝ°жІүзқЎгҖӮжӣјзү№е°јдәҡдёҚеҸӘжҳҜеҶҚзҺ°дәӢ件пјҢд»–з”ЁвҖңи·қзҰ»вҖқжқҘеёғзҪ®пјҡеӨ©дёҺең°гҖҒиҖ¶зЁЈдёҺй—Ёеҫ’гҖҒзҘ·е‘ҠдёҺжӯҰеҷЁгҖҒиӯҰйҶ’дёҺжІүзқЎвҖ”вҖ”йӮЈдёҖйҒ“йҒ“й—ҙйҡ”ж”Ҝй…ҚдәҶж•ҙдёӘз”»йқўгҖӮйӮЈй—ҙйҡ”д»ҝдҪӣжҠҠ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үҖиҜҙвҖңеӯӨзӢ¬зҡ„еҚҒеӯ—жһ¶д№Ӣи·ҜвҖқзҝ»иҜ‘жҲҗдәҶи§Ҷи§үиҜӯиЁҖгҖӮз«ҷеңЁиҝҷе№…з”»еүҚпјҢжҲ‘们еҫҲйҡҫдёҚй—®пјҡжҲ‘з«ҷеңЁе“ӘйҮҢпјҹеңЁиҖ¶зЁЈзҘ·е‘Ҡзҡ„иҝ‘ж—ҒпјҢиҝҳжҳҜеңЁзқЎж„Ҹзҡ„иҲ’йҖӮйҮҢпјҢжҠ‘жҲ–еңЁиғҢеҸӣзҡ„йҳҹдјҚдёӯпјҹ
еҪ“жҲ‘们еҶҚж¬Ўжғіиө·жӣјзү№е°јдәҡзҡ„жһ„еӣҫпјҢз”»йқўдёӢж–№жІүзқЎзҡ„й—Ёеҫ’дёҚеҶҚеҸӘжҳҜжҮ’ж•Јзҡ„дәәпјҢиҖҢеғҸжҲ‘们дёҚж–ӯйҮҚжј”зҡ„жӮІеү§жЁЎејҸпјҡжҲ‘们иҜҙж„ҝж„ҸдёәжүҖзҲұзҡ„дәәвҖңеҒҡд»»дҪ•дәӢвҖқпјҢеҚҙеңЁд»–жңҖиҪҜејұзҡ„йӮЈдёҖеӨңпјҢиҝһеқҗеңЁж—Ғиҫ№зҡ„еҠӣж°”йғҪжІЎжң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·қзҰ»ж„ҹдёҚиҜҘд»ҘиҮӘиҙЈж”¶е°ҫпјӣи·қзҰ»ж„ҹеә”еҪ“жҢҮеҮәжӮ”ж”№зҡ„ж–№еҗ‘вҖ”вҖ”еҗ‘иҖ¶зЁЈйқ иҝ‘пјҢеҗ‘зҘ·е‘Ҡйқ иҝ‘пјҢеҗ‘вҖңиӯҰйҶ’зҡ„е®һи·өвҖқиҝҲдёҖжӯҘгҖӮиҖҢиҝҷдёҖжӯҘдёҚеҝ…е®ҸеӨ§пјҡжҜҸеӨ©е“ӘжҖ•еҚҒеҲҶй’ҹпјҢе®үйқҷеқҗдёӢе‘је”ӨвҖңйҳҝзҲёзҲ¶вҖқпјӣжҠҠеҪ“еӨ©зҡ„жғ§жҖ•дёҺж¬ІжңӣдёҚйҡҗи—Ҹең°е‘ҲдёҠпјӣжңҖеҗҺз”ЁвҖңз…§дҪ зҡ„ж„ҸжҖқвҖқжҠҠеҝғзҡ„ж–№еҗ‘еӣәе®ҡдҪҸвҖ”вҖ”иҝҷе°ұжҳҜжҠҠе®ўиҘҝ马尼зҡ„зҘ·е‘Ҡз»ӯеҶҷиҝӣд»Ҡж—ҘиҜӯиЁҖйҮҢжңҖзҺ°е®һзҡ„ж–№ејҸгҖӮ
еҪ’ж №еҲ°еә•пјҢеј еӨ§еҚ«зү§еёҲжғіи®©жҲ‘们еңЁе®ўиҘҝ马尼зңӢи§Ғзҡ„并дёҚжҳҜвҖңз—ӣиӢҰвҖқжң¬иә«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з—ӣиӢҰдёӯд»ҚдёҚеҙ©ж–ӯзҡ„е…ізі»д№Ӣз»ігҖӮеҚҒеӯ—жһ¶дёҚжҳҜиҖ¶зЁЈз”ҹе‘ҪйҮҢзӘҒ然й—Ҝе…Ҙзҡ„жӮІеү§пјҢиҖҢжҳҜзҲұзҡ„иҝһиҙҜжҖ§иў«жҺЁиҝӣеҲ°жңҖеҗҺ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ӣиҝҷд»ҪиҝһиҙҜжҖ§еңЁе®ўиҘҝ马尼被зҘ·е‘ҠеЎ‘еҪўпјҢеңЁиў«жҚ•ж—¶жҳҫдёәдёҚеҠЁж‘Үзҡ„еқҰ然пјҢжңҖз»ҲеңЁеҗ„еҗ„д»–зҡ„иҲҚе·ұдёӯе®ҢжҲҗ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ӣӣж—¬жңҹзҡ„й»ҳжғідёҚдјҡеҒңеңЁйҳҙйғҒйҮҢпјӣе®ғжӣҙиҰҒжҲ‘们зңӢи§Ғпјҡз©ҝиҝҮжңҖй»‘зҡ„еӨңзҡ„йЎәжңҚпјҢдјҡејҖеҗҜжҖҺж ·зҡ„жё…жҷЁпјҢиҖҢйӮЈжё…жҷЁеҰӮдҪ•д»ҘвҖңеӨҚжҙ»вҖқд№ӢеҗҚдҪҝжҲ‘们еҶҚеәҰжҙ»иҝҮжқҘгҖӮ并且пјҢйӮЈеӨҚжҙ»зҡ„е…үпјҢдјҡеңЁдёҚйҖғйҒҝе®ўиҘҝ马尼еҺӢжҰЁзҡ„дәәиә«дёҠпјҢжҠҳе°„еҫ—жӣҙжё…жҷ°гҖ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