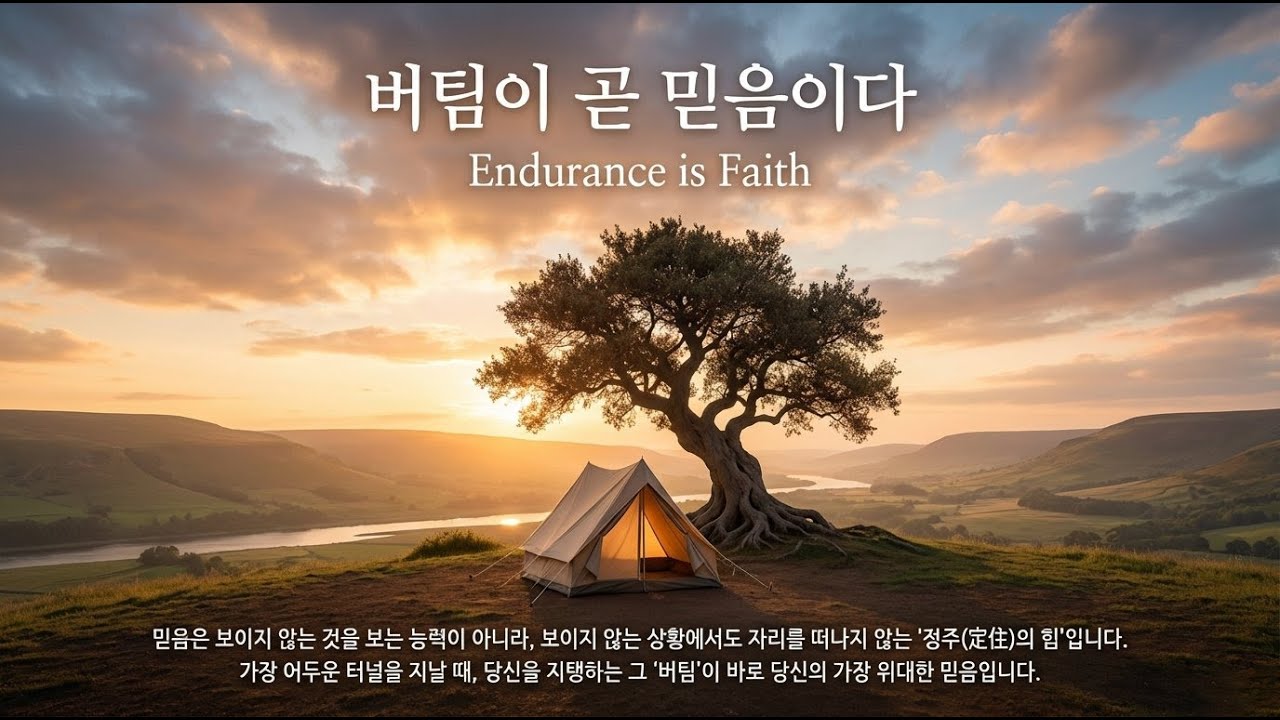У┐ЎТў»СИђу»ЄС╗Ц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У«▓УДБжЕгтЈ»удЈжЪ│угг14уФаРђюТЅЊуа┤ждЎУєЈујЅуЊХРђЮС║ІС╗ХуџёУ«▓жЂЊСИ║тЪ║уАђуџёТќЄуФа№╝їС╗јуЦътГдсђЂУЅ║Тю»сђЂжЪ│С╣љСИју╗ЈтЁИуГЅтцџжЄЇУДњт║д№╝їуФІСйЊтю░жўљжЄіС║єуюІС╝╝ТхфУ┤╣уџёуѕ▒уџётЦЦуДўсђЂтіауЋЦС║║уі╣тцДуџёТѓ▓тЅД№╝їС╗ЦтЈіСИ║УђХуеБт«ЅУЉгСйюжбётцЄуџёС╝»тцДт░╝тЦ│тГљуџёуї«У║ФсђѓтђЪуЮђУ┐ЎТ«хУхиС║јС╝»тцДт░╝жЋ┐тцДж║╗жБјУђЁУЦ┐жЌет«ХуџёТЋЁС║І№╝їжЄЇТќ░У┐йжЌ«С╗іТЌЦТѕЉС╗гуџёТЋгТІюСИјтЦЅуї«№╝їС╗ЦтЈіуѕ▒уџёТюгУ┤е№╝їТў»СИђу»ЄТъЂтЁиТи▒т║дуџёуЂхС┐«ТЋБТќЄсђѓ
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уџёУ«▓жЂЊ№╝їТюЅСИђСИфуІгуЅ╣уџёжГЁтіЏ№╝їт░▒Тў»Тђ╗УЃйС╗јтЄ║С║║ТёЈТќЎуџёУДњт║дтИдТѕЉС╗гжЄЇТќ░тЄЮУДєжѓБС║Џти▓Уђ│уєЪУЃйУ»дуџёу╗ЈТќЄсђѓУ┐ътљїТаиУ«░УййтюежЕгтЈ»удЈжЪ│угг14уФаСИГуџёРђюждЎУєЈујЅуЊХРђЮС║ІС╗Х№╝їСИђТЌду╗ЈУ┐ЄС╗ќуџёТЅІ№╝їт░▒СИЇтєЇтЈфТў»СИђТ«ху«ђуЪГуџёТЈњТЏ▓№╝їУђїТў»УбФтАЉжђаТѕљСИђтЄ║ТЌХжЌ┤СИјуЕ║жЌ┤сђЂС║║у▒╗т┐ЃуљєСИјуЂхуЋїу▓Йт»єС║цу╗ЄуџёуЦътюБТѕЈтЅД№╝џС╝»тцДт░╝жЋ┐тцДж║╗жБјУђЁУЦ┐жЌеуџёт«Х№╝їжЮЎжЮЎУх░У┐ЏжѓБт▒ІтєЁсђЂТЅЊуа┤ујЅуЊХуџёжѓБСйЇтЦ│тГљ№╝їуюІУДЂУ┐ЎСИђт╣ЋСЙ┐ТёцТђњУ«Ау«ЌуџёжЌетЙњтњїтіауЋЦС║║уі╣тцД№╝їТюђтљј№╝їУ┐ўТюЅжѓБСйЇТііУ┐Ўтю║ТхфУ┤╣т«БтЉіСИ║СИ║УЄфти▒т«ЅУЉгТЅђСйюжбётцЄуџёУђХуеБуџётБ░жЪ│сђѓУ┐ЎС║Џућ╗жЮбтй╝ТГцС║цжћЎ№╝їСй┐У┐Ўу»ЄУ«▓жЂЊУЄфуёХУђїуёХтю░тљЉТ┤╗тюеС╗іТЌЦуџёТѕЉС╗гуџёС┐АС╗░СИјућЪТ┤╗№╝їТіЏтЄ║уіђтѕЕуџёжЌ«жбўсђѓ
ТЋЁС║ІуџёУѕътЈ░У«ЙтюеУђХУи»ТњњтєитЇЂтГЌТъХС║ІС╗ХтЅЇСИЇУ┐ЄтЄатцЕ№╝їСИђСИфтЈФС╝»тцДт░╝уџёт░ЈТЮЉт║ёсђѓтюБу╗ЈуЅ╣ТёЈтИдуЮђС╗ќУ┐Єтј╗уџёС╝цуЌЋ№╝їуД░жѓБжЄїСИ║РђюТѓБж║╗жБјуЌЁуџёУЦ┐жЌеуџёт«ХРђЮсђѓтюетйЊТЌХ№╝їж║╗жБјуЌЁТў»уцЙС╝џСИјт«ЌТЋЎжџћуд╗уџёУ▒АтЙЂРђћРђћжѓБТў»УбФТјетѕ░тЁ▒тљїСйЊС╣ІтцќуџёС║║№╝їУбФТјњжЎцтюеуѕ▒СИјУДдТЉИС╣ІтцќуџёС║║сђѓуёХУђїУђХуеБС║▓УЄфУх░тѕ░С╗ќуџёжЮбтЅЇ№╝їУ┐ЏтЁЦС╗ќуџёт«Х№╝їтюеС╗ќуџёжЦГТАїТЌЂСИјС╗ќСИђтљїтљЃтќЮсђ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тюеУ┐ЎуЪГуЪГуџёУАеУЙЙжЄї№╝їуюІУДЂС║єудЈжЪ│уџёт┐ЃУёЈ№╝џтјЪТюгСИЇТЄѓСйЋСИ║уѕ▒уџёуЂхжГѓ№╝їУбФтї╗Т▓╗С╣Ітљј№╝їтдѓС╗іуФЪТѕљС║єТЉєУ«ЙТёЪТЂЕуГхтИГуџёС║║сђѓУЦ┐жЌеуџёт«ХСИЇтєЇТў»РђюСИЇТ┤ЂС╣ІС║║РђЮуџёуЕ║жЌ┤№╝їУђїТў»УњЎТЂЕС╣ІС║║ТЉєСИіТёЪТЂЕС╣ІуГхуџётюБТ┤Ђтю║ТЅђсђѓ
т░▒тюежѓБуГхтИГтйЊСИГ№╝їСИђСйЇТЌатљЇуџётЦ│тГљУх░С║єУ┐ЏТЮЦсђѓжЕгтЈ»удЈжЪ│У«ЕтЦ╣С┐ЮТїЂтї┐тљЇ№╝їСйєу║ду┐░удЈжЪ│тЇ┤тЉіУ»ЅТѕЉС╗г№╝їУ┐ЎтЦ│тГљТГБТў»ТІЅТњњУи»уџётд╣тд╣жЕгтѕЕС║џсђѓтЏЏтЇиудЈжЪ│С╣джЃйС╗јСИЇтљїуџёУДњт║д№╝їУ«░УййС║єСИђСйЇтЦ│тГљтљЉУђХуеБТхЄтЦаждЎУєЈуџёТЋЁС║І№╝џжЕгтцфтњїжЕгтЈ»У«░СИІуџёТў»№╝їтюеС╝»тцДт░╝УЦ┐жЌет«ХСИГ№╝їТюЅС║║ТііждЎУєЈТхЄтюеУђХуеБуџётц┤СИі№╝ЏУи»тіаТЈЈу╗ўуџёТў»№╝їСИђСИфуйфС║║тЦ│тГљтюеТ│ЋтѕЕУхЏС║║уџёт«ХжЄї№╝їт░єждЎУєЈтњїую╝Т│фТхЄтюеУђХуеБуџёУёџСИі№╝Џу║ду┐░тѕЎУ«░тйЋС╝»тцДт░╝уџёжЕгтѕЕС║џућеждЎУєЈТхИТХдУђХуеБуџёУёџ№╝їтЈѕућетц┤тЈЉтј╗ТЊдТІГуџёТЃЁТЎ»сђѓТЌХжЌ┤СИјтю░уѓ╣УЎйСИЇт░йуЏИтљї№╝їСйєТ»ЈСИфТЋЁС║ІуџёСИГт┐Ѓ№╝їжЃйу┤Ду┤ДтЏ┤у╗ЋуЮђРђюТъЂтЁХТўѓУ┤хуџёждЎУєЈРђЮСИјРђюуюІУхиТЮЦтЃЈТхфУ┤╣уџёуѕ▒РђЮсђ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С╗ЦУ┐ЎтЄатЇиудЈжЪ│С╣дуџётцџжЄЇтБ░жЃеСИ║УЃїТЎ»№╝їу╗єУЄ┤тю░тЄЮУДєжЕгтЈ»удЈжЪ│угг14уФауџёУ┐ЎС╗ХС║Ісђѓ
тЦ╣ТЅІжЄїТІ┐уЮђуџёТў»СИђуЊХРђюТъЂУ┤хуџёуюЪтЊфтЊњждЎУєЈРђЮсђѓтЊфтЊњТў»СИђуДЇС╗јтќюжЕгТІЅжЏЁСИђтИдУ┐ЏтЈБуџёжФўу║ДждЎТќЎ№╝їтюеТЎ«жђџт«Хт║ГтЄаС╣јжџЙС╗ЦУДдуб░№╝їТјЦУ┐ЉтЦбСЙѕтЊЂсђѓТїЅудЈжЪ│С╣дуџёУ«░Уйй№╝їУ┐ЎуЊХждЎУєЈтђ╝СИЅуЎЙтцџуггу║│жЄї№╝їСИђуггу║│жЄїТў»тйЊТЌХТЎ«жђџтиЦС║║СИђтцЕуџётиЦжњ▒№╝їжЎцтј╗т«ЅТЂ»ТЌЦтњїУіѓТюЪСИЇУЃйтЂџтиЦуџёТЌЦтГљ№╝їУ┐ЎтЄаС╣јуЏИтйЊС║јТЋ┤ТЋ┤СИђт╣┤уџётиЦУхё№╝їТў»СИђугћтиеТгЙсђѓтЦ│тГљт╣ХТ▓АТюЅтЈфтђњтЄ║СИђуѓ╣уѓ╣ТЮЦуће№╝їтЦ╣ТііујЅуЊХТюгУ║ФТЅЊтЙЌу▓Ѕубј№╝їт░єТЋ┤уЊХждЎУєЈСИђТгАТђДТхЄтюеУђХуеБуџётц┤тњїУёџСИісђѓУ┐ЎТў»СИђСИфтєЇС╣ЪТћХСИЇтЏъТЮЦуџётє│т«џсђЂСИђСИфТЌаТ│ЋжђєУйгуџёжђЅТІЕ№╝їТў»тЦ╣СИђућЪТЅђтЂџтЄ║ТюђТўѓУ┤хуџёСИђТгАУАїтіесђѓ
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т╣ХСИЇТііУ┐ЎујЅуЊХС╗ЁС╗ЁУДєСйюСИђС╗ХжФўу║ДтїќтдєтЊЂ№╝їУђїТў»У»╗ТѕљУ┐ЎСйЇтЦ│тГљСИђућЪТіЊтюеТЅІжЄїсђЂС╗БУАетЦ╣тЁежЃеУ║ФтѕєсђЂт«ЅтЁеТёЪСИјТюфТЮЦуџёУ▒АтЙЂсђѓтюети┤тІњТќ»тЮдуџёТќЄтїќжЄї№╝їу╗Ўт░іУ┤хуџёт«бС║║тђњСИіРђюСИђуѓ╣РђЮждЎУєЈ№╝їжЂЊТў»уц╝Уіѓ№╝їтЇ┤У┐юУ┐юТ▓АТюЅтѕ░У┐ЎуДЇтю░ТГЦсђѓУ┐ЎСйЇтЦ│тГљУиеУ┐ЄС║єуц╝УіѓуџёуЋїу║┐№╝їУ┐ЏтЁЦС║єуцЙС╝џтИИУ»єтњїу╗ЈТхјжђ╗УЙЉТЅђТЌаТ│ЋТјДтѕХуџёжбєтЪЪРђћРђћС╣Ът░▒Тў»уѕ▒уџёРђюУ┐ЄжЄЈРђЮсђѓТГБтЏаСИ║У┐ЎС╗йУ┐ЄжЄЈ№╝їУ┐ЎС╗йуѕ▒уФІтѕ╗УбФУ┤┤СИіС║єРђюТхфУ┤╣РђЮуџёТаЄуГЙсђѓжЌетЙњТёцТёцСИЇт╣│тю░У»┤тЄ║уџёУ»Ю№╝їС╗ітцЕтљгТЮЦТѕЉС╗гС╣Ът╣ХСИЇжЎїућЪ№╝џРђюСИ║С╗ђС╣ѕУ┐ЎТаиТхфУ┤╣ждЎУєЈтЉб№╝ЪУ┐ЎждЎУєЈтЈ»С╗ЦтЇќСИЅуЎЙтцџуггу║│жЄї№╝їтЉеТхјуЕиС║║СИЇТЏ┤тЦйтљЌ№╝ЪРђЮС╗ќС╗гуџёУ»ЮУ»ГУАежЮбСИіТўЙтЙЌТГБС╣ЅсђЂтљѕС╣јС╝дуљєсђЂТъЂТюЅу╗ЈТхјтц┤УёЉсђѓуёХУђїУ«▓жЂЊУђЁТЂ░ТЂ░тюеТГцТїЄтЄ║№╝џжЌетЙњт▒ъуЂхуџёТёЪт«ўти▓у╗Јж║╗ТюеС║єсђѓтюеС╗ќС╗гую╝СИГ№╝їТ»ћУхиуї«у╗ЎУђХуеБуџёуѕ▒ТюЅтцџТи▒№╝їждЎУєЈуџёС╗иуГЙТЏ┤тЁѕТўатЁЦую╝тИў№╝ЏТ»ћУхиуї«У║ФуџёУігУі│№╝їС║ЈТЇЪСИјТћХуЏіуџёУ«Ау«ЌТўЙтЙЌТЏ┤тіатиетцДсђѓ
у║ду┐░удЈжЪ│У┐ЏСИђТГЦтЉіУ»ЅТѕЉС╗г№╝їуюЪТГБТііУ┐ЎуЋфТі▒ТђеУ»┤тЄ║тЈБуџёС║║№╝їт░▒Тў»тіауЋЦС║║уі╣тцДсђѓС╗ќУ»┤№╝џРђюСИ║С╗ђС╣ѕСИЇТііУ┐ЎждЎУєЈтЇќСИЅуЎЙтцџуггу║│жЄї№╝їтЉеТхјуЕиС║║тЉб№╝ЪРђЮтЈ»удЈжЪ│С╣дтЇ┤тєижЮЎтю░Т│еУДБУ»┤№╝їС╗ќУ┐ЎТаиУ»┤т╣ХСИЇТў»тЏаСИ║уюЪт┐ЃТїѓт┐хуЕиС║║№╝їУђїТў»тЏаСИ║С╗ќТјїу«Ажњ▒тЏі№╝їтЈѕтИИтЈќтЁХСИГТЅђтГўуџёсђѓт░▒тюетЦ│тГљуџёуѕ▒СИјуі╣тцДуџёуЏўу«ЌС╣ІжЌ┤№╝їУБѓу╝ЮУбФТИЁТЦџтю░ТўЙжю▓тЄ║ТЮЦсђ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тљїТЌХУЂћТЃ│тѕ░у║ду┐░удЈжЪ│13уФа2УіѓжѓБтЈЦ№╝џРђюжГћжг╝ти▓у╗Јт░єтЇќУђХуеБуџёТёЈт┐хТћЙтюетіауЋЦС║║УЦ┐жЌеуџётё┐тГљуі╣тцДт┐ЃжЄїсђѓРђЮС╗ќТїЄтЄ║№╝їтЄАТў»уюЪт«ъуџёуѕ▒ТўЙТўјС╣Ітцё№╝їтЇ┤У«ЕС║║ТёЪтѕ░СИЇУѕњТюЇсђЂт┐ЇСИЇСйЈтіаС╗ЦТїЄУ┤БуџёжѓБуДЇт┐ЃТђЂ№╝їТГБТў»ТњњСйєжњ╗У┐ЏТЮЦуџёу╝ЮжџЎсђѓСИђСИфСИЇУЃйућеуѕ▒тј╗ТјЦу║│уѕ▒уџёт┐Ѓ№╝їтЈфУЃйТііуї«У║ФуюІТѕљТхфУ┤╣уџёую╝уЮЏ№╝їТюђу╗ѕС╝џТііС║║СИђТГЦТГЦТјетљЉтЃЈуі╣тцДжѓБТаиуџёУЃїтЈЏсђѓ
У┐ЎуДЇж▓юТўјуџёт»╣Т»ћ№╝їСИЇС╗ЁтюеуЦътГджбєтЪЪСИГтЈЇтцЇУбФТЈљУхи№╝їС╣ЪСИЇТќГтюеУЅ║Тю»СИјжЪ│С╣љуџёСИќуЋїжЄїУбФтЈўтЦЈсђѓСЙІтдѓ№╝їТЎ«ТІЅтцџтЇџуЅЕждєТЅђУЌЈСИђт╣Ё17СИќу║фуџёу┤аТЈЈсђіMary
Magdalen at the Feet of ChristсђІСИГ№╝їжѓБСйЇУбФУ«цСИ║Тў»Ті╣тцДТІЅжЕгтѕЕС║џуџётЦ│тГљУифтюетю░СИі№╝їС║▓тљ╗тЪ║уЮБуџёУёџ№╝ЏтЮљтюетИГжЌ┤СИіСйЇуџёУђХуеБУ║ФТЌЂ№╝їтѕЎућ╗уЮђтЄаСИфТ╗АУёИТЃіУ«ХтЈѕуЋЦтИдСИЇТѓдсђЂтљЉС╗ќТ»ћтѕњТЅІті┐уџёС║║уЅЕсђѓУ┐Ўт╣ЁТііУи»тіаудЈжЪ│СИГРђюуйфтдЄтюеУђХуеБУёџтЅЇтђЙтђњую╝Т│фСИјждЎУєЈРђЮуџётю║ТЎ»УДєУДЅтїќуџёСйютЊЂ№╝їТъЂтЁХТхЊу╝Етю░тЉѕуј░тЄ║жѓБуДЇуЕ┐УХіУ┤БжџЙСИјУй╗УћЉ№╝їтЈфтЇЋтЇЋТ│еуЏ«СИ╗уџёуї«У║ФтД┐ТђЂсђѓтюетйЊС╗БУ«ИтцџС╗ЦРђюжЕгтѕЕС║џтюеУђХуеБУёџтЅЇтђњждЎУєЈРђЮСИ║СИ╗жбўуџётЪ║уЮБТЋЎу╗ўућ╗СИГ№╝їС╣ЪТў»тдѓТГц№╝џу┤Ду┤ДТіЊСйЈУђХуеБтЈїУёџсђЂТћЙтБ░уЌЏтЊГуџётЦ│тГљ№╝їСИјуФЎтюетљјТќ╣уџ▒уЮђуюЅтц┤уџёуі╣тцД№╝їУбФСИђтєЇт»╣уЁД№╝Џуѕ▒СИјУ┤фтЕфсђЂТЋгТІюСИјУ«Ау«Ќуџётє▓Тњъ№╝їУбФт╝║уЃѕтю░УАеуј░тЄ║ТЮЦсђѓ
тюежЪ│С╣љтйЊСИГ№╝їУ┐ЎТ«ху╗ЈТќЄС╣ЪТюЅуЮђжЮътљїт»╗тИИуџётѕєжЄЈсђѓу║ду┐░┬итАъти┤Тќ»Уњѓт«Ѕ┬ити┤УхФуџёсђіжЕгтцфтЈЌжџЙТЏ▓сђІ№╝їТў»СЙЮтЙфжЕгтцфудЈжЪ│тЈЌжџЙУ«░тЈЎУђїтєЎТѕљуџёСИђжЃеС╝ЪтцДС┐АС╗░ТИЁтћ▒тЅД№╝їт«ЃтюеудЈжЪ│тЈЎС║ІСИјС╝џС╝ЌтєЁт┐ЃтЏът║ћС╣ІжЌ┤ТЮЦтЏъС║цу╗ЄсђѓтЁХу╗ЊТъёСИГ№╝їтюетЅЇТ«хСЙ┐т«ЅТјњС║єС╝»тцДт░╝УєЈТі╣уџётю║ТЎ»№╝їу┤ДТјЦуЮђуџётљѕтћ▒сђѕWozu dienet dieser Unrat?сђЅ№╝ѕРђюУ┐ЎуДЇТхфУ┤╣ТюЅС╗ђС╣ѕуће№╝ЪРђЮ№╝Ѕ№╝їућ▒тљѕтћ▒тЏбС╗БТЏ┐ТёцТђњуџёжЌетЙњ№╝їтћ▒тЄ║С╗ќС╗гуџётЪІТђесђѓжџЈтљј№╝їТў»удЈжЪ│С╣дТюЌУ»хУђЁСИјУђХуеБуџёт«БтЈЎУ░ЃуЏИу╗ДУђїТЮЦ№╝їУђХуеБтЏъуГћУ»┤№╝џТў»тЦ╣СИ║ТѕЉуџёт«ЅУЉгжбётЁѕСйюС║єтЄєтцЄсђѓТГБтд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тюеУ«▓жЂЊСИГСИђтєЇт╝║У░Ѓуџё№╝џтюеСИќС║║тњїжЌетЙњую╝СИГУбФУДєСйюТхфУ┤╣уџёУАїСИ║№╝їтюеУђХуеБую╝СИГтЇ┤УбФжЄЇТќ░У»ажЄіСИ║СИ║УЄфти▒С╣ІТГ╗ТЅђСйюуџёуЙјтЦйуї«У║Фсђѓти┤УхФућетБ░жЪ│уџёт╝атіЏСИјУѕњт▒ЋУАеУЙЙС║єУ┐ЎуЋфуЦътГдуџёжЄЇжЄі№╝їУђїУ«▓жЂЊУђЁтѕЎТііУ┐ЎжЄЇжЄіТІќтЁЦТѕЉС╗гС╗іТЌЦуџёТЋгТІюСИјућЪТ┤╗С╣ІСИГ№╝їУ«ЕТѕЉС╗гтєЇСИђТгАтЈЉжЌ«сђѓ
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т╣ХСИЇТііУ┐ЎтЦ│тГљуџёСИЙтіеуюІТѕљСИђТЌХТЃЁу╗фуџёуѕєтЈЉ№╝їУђїТў»УДєСИ║СИђуДЇт▒ъуЂхуџёуЏ┤УДЅРђћРђћтЦ╣жбёТёЪтѕ░УђХуеБуџёТГ╗С║АСИјт«ЅУЉг№╝їт╣ХС╗ЦУАїтіеСйютЄ║тЏът║ћсђѓУђХуеБжѓБтЈЦРђютЦ╣Тў»СИ║ТѕЉт«ЅУЉгС╣ІТЌЦжбётЁѕТііждЎУєЈжбётцЄтЦйРђЮСИГ№╝їУЋ┤тљФуЮђуЦѓТЋ┤СИфС║║ућЪУбФтјІу╝ЕТѕљСИђтЈЦУ»Ю№╝џуЦѓСИђућЪт░▒Тў»СИђТ«хСИ║ТѕЉС╗гУђїТ┤╗уџёуѕ▒уџёТЌЁуеІ№╝їУђїУ┐ЎТЌЁуеІуџёу╗ѕуѓ╣№╝їт░▒Тў»тЇЂтГЌТъХСИіуџёТГ╗С║АсђѓждЎУєЈтјЪТюгТў»С║║ТГ╗тљј№╝їСИ║тЁХУ║ФСйЊТ┤ЌтЄђт╣ХТХѓТі╣уџёУі│ждЎТЋгТёЈсђѓтЦ│тГљтюетЇЂтГЌТъХС║ІС╗ХУ┐ўТюфтЈЉућЪС╣ІтЅЇ№╝їСЙ┐ТііС╣ЪУ«ИТў»УЄфти▒ТюђтљјСИђТгАуџёТю║С╝џТЈљтЅЇ№╝їућетЦ╣ТЅђТІЦТюЅТюђуЈЇУ┤хуџёСИюУЦ┐№╝їжбётЁѕТхЄтюеСИ╗уџёУ║ФСйЊСИісђѓУ┐ЎТў»тЈфТюЅТЋЈжћљТёЪтЈЌтѕ░ТЅђуѕ▒С╣ІС║║ТГ╗ТюЪт░єУ┐ЉуџёС║║№╝їТЅЇС╝џСйютЄ║уџёРђюж▓ЂУјйРђЮС╣ІСИЙсђѓУ┐ЎуюІС╝╝ТхфУ┤╣уџёСИЙтіе№╝їС╣ЪжџљжџљжбёУАеС║єУђХуеБУЄфти▒уџётЉйУ┐љ№╝џтюетЇЂтГЌТъХСИі№╝їуЦѓУдЂРђюУбФТЅЊубјсђЂУбФтђЙтђњРђЮ№╝їТііУЄфти▒уџёУ║ФСйЊтњїт«ЮУАђтйЊСйюуѕ▒т«їтЁеуї«СИісђѓ
У«▓жЂЊтюеУ┐ЎжЄїУЄфуёХтю░ТхЂтљЉУи»тіаудЈжЪ│угг15уФаРђћРђћУ┐итц▒уџёуЙісђЂтц▒УљйуџёжЊХтИЂтњїТхфтГљуџёТ»ћтќ╗сђѓуЅДС║║ТііжѓБС╣ЮтЇЂС╣ЮтЈфуЙіуЋЎтюеТЌижЄј№╝їтј╗т»╗ТЅЙжѓБтЈфтц▒УљйуџёСИђтЈф№╝ЏтдЄС║║ТЅЙтЏъжЂЌтц▒уџёСИђтЮЌжњ▒тИЂ№╝їт░▒ТІЏУЂџжѓ╗УѕЇТЉєУ«ЙуГхтИГт║єуЦЮ№╝ЏуѕХС║▓СИ║жѓБСИфТїЦжюЇт«ХС║ДтљјтйњТЮЦуџётё┐тГљ№╝їТ»ФСИЇтљЮТЃютю░ТІ┐тЄ║СИітЦйуџёУбЇтГљсђЂТѕњТїЄтњїУѓЦуЅЏуііТЮЦТгЙтЙЁсђѓС╗ќС╗гуџёС╗╗СйЋСИђСИфСИЙтіе№╝їжЃйТЌаТ│Ћућеу╗ЈТхјтГдуџёжђ╗УЙЉТЮЦУДБжЄі№╝їтЁежЃежЃйТў»РђюСИЇуљєТђДРђЮРђюСИЇжФўТЋѕРђЮуџёуѕ▒сђѓуёХУђїУђХуеБТ»ФСИЇуі╣У▒Фтю░ТїЄтљЉУ┐ЎС╗йРђюСйјТЋѕујЄРђЮуџётиЁт│░РђћРђћжѓБт░▒Тў»СИітИЮУЄфти▒сђѓуѕ▒Тђ╗Тў»Т║бтЄ║У«Ау«ЌуџёУЙ╣уЋї№╝їУђїУ┐ЎТ║бтЄ║уџёжЃетѕє№╝їтюеТЌЂС║║ую╝СИГт░▒тЈФСйюРђюТхфУ┤╣РђЮсђ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СИђжњѕУДЂУАђтю░ТїЄтЄ║№╝џтйЊт╣┤С╝ЂтЏЙТХѕжЎцУ┐ЎуДЇРђюТхфУ┤╣РђЮуџёС║║№╝їТў»жѓБС║ЏжЌетЙњ№╝їУђїС╗ітцЕС╣ЪтЙѕтЈ»УЃйт░▒Тў»ТѕЉС╗гУЄфти▒сђѓжЌ«жбўСИЇтюеС║јУ┤БС╗╗ТёЪтњїТЋѕујЄТюгУ║Ф№╝їУђїтюеС║јтйЊт«ЃС╗гУбФТћЙтюеуѕ▒С╣ІтЅЇ№╝їТѕљСИ║УААжЄЈСИђтѕЄуџёждќУдЂТаЄтЄєТЌХ№╝їуюЪТГБуџётЇ▒жЎЕт░▒тЄ║уј░С║єсђѓ
С╗ќС╣ЪтєижЮЎтю░ТЈГуц║№╝їС╗іТЌЦТѕЉС╗гуџёС┐АС╗░СйЋуГЅт«╣ТўЊУбФСИђуДЇРђюуі╣тцДт╝ЈуџёуљєТђДРђЮТЅђС┐ўУјисђѓУ»┤тѕ░ТЋгТІюуџёТЌХжЌ┤сђЂуї«У║Фуџёті│УІдсђЂжЄЉжњ▒уџёСй┐ућесђЂС║ІтиЦуџёТъюТЋѕ№╝їТѕЉС╗гТюгУЃйтю░т░▒С╝џТІ┐тЄ║РђюТЋѕујЄРђЮРђюТѕљТъюРђЮРђюТіЋтЁЦСИјС║ДтЄ║Т»ћРђЮУ┐ЎТаиуџёУ»ЇТ▒ЄсђѓУ┐ЎС║ЏУ»ГУеђтюеу╗ЈУљЦу╗ёу╗ЄтњїжА╣уЏ«ТЌХтЏ║уёХт┐ЁУдЂ№╝їСйєСИђТЌдУбФућеСйюУААжЄЈуѕ▒ТюгУ║Фуџёт░║т║д№╝їТЋгТІют░▒уФІтѕ╗тЈўТѕљС║єтє░тєиуџёУ»ёС╝░сђ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У»┤№╝џРђюуѕ▒СИђтєиТиА№╝їТѕЉС╗гт░▒С╝џтЈўтЙЌУХіТЮЦУХіУЂфТўјсђЂУХіТЮЦУХіу«ЌУ«АсђѓРђЮС╗ќУГдтЉіТѕЉС╗г№╝їТ»ћУхиУЂфТўјТюгУ║Ф№╝їТЏ┤тЈ»ТђЋуџёТў»тц▒тј╗уѕ▒уџёУЂфТўјсђѓтЦ│тГљуџёУАїСИ║Т»ФТЌауќЉжЌ«Тў»СИЇтљѕжђ╗УЙЉуџё№╝їтЈ»ТГБтЏаУ┐ЎС╗йРђюСИЇтљѕжђ╗УЙЉРђЮ№╝їУђХуеБТЅЇт«БтЉі№╝џРђютЦ╣тюеТѕЉУ║ФСИітЂџуџёТў»СИђС╗ХуЙјС║ІсђѓРђЮт╣Хт║ћУ«ИУ»┤№╝їТЌаУ«║удЈжЪ│С╝атѕ░СИќуЋїСйЋтцё№╝їжЃйУдЂУ┐░У»┤У┐ЎтЦ│тГљТЅђУАїуџё№╝їС╗ЦУ«░т┐хтЦ╣сђѓ
тЈдСИђТќ╣жЮб№╝ї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УЄфти▒уџёС║║ућЪ№╝їС╣ЪтљїТаит▒Ћуј░тЄ║уѕ▒СИју╗ЊТъёсђЂуї«У║ФСИјтѕХт║дС╣ІжЌ┤уџёт╝атіЏсђѓС╗ќТў»тЄ║У║ФжЪЕтЏйуџёуЦътГдт«ХтњїуЅДУђЁ№╝їтѕЏуФІС║єтїЁТІгуЙјтЏйуџё Olivet University тюетєЁуџётцџТЅђтЪ║уЮБТЋЎТЋЎУѓ▓СИјт«БТЋЎТю║ТъёС╗ЦтЈітфњСйЊС║ІтиЦсђѓУ┐ЎС║Џт▒ЦтјєУ»┤Тўј№╝їС╗ќт╣ХСИЇТ╗АУХ│С║јТііуѕ▒тЂюуЋЎтюеуѓйуЃГТЃЁТёЪуџёт▒ѓжЮб№╝їУђїТў»У»ЋтЏЙтђЪуЮђТЋЎУѓ▓сђЂС╝атфњтњїт«БТЋЎуџёТъХТъё№╝їТііуѕ▒у╗ёу╗ЄТѕљтЈ»ТїЂу╗Гуџёуї«У║ФсђѓуёХУђї№╝їтЇ│СЙ┐тдѓТГц№╝їС╗ќтюеУ┐Ўу»ЄУ«▓жЂЊСИГСИђтєЇт╝║У░ЃуџётЇ┤тЙѕТИЁТЦџ№╝џС╗╗СйЋтѕХт║дтњїС║ІтиЦ№╝їтЈфУдЂтц▒тј╗С║єС╝»тцДт░╝тЦ│тГљТЅђуц║УїЃуџёжѓБжбЌТЌаТЮАС╗ХсђЂУ┐ЉС╣јж▓ЂУјйуџёуѕ▒С╣Іт┐Ѓ№╝їт░▒жџЈТЌХтЈ»УЃйТ▓дСИ║СИјуі╣тцДт╝ЈУ«Ау«ЌтѕФТЌаС║їУЄ┤уџёуЕ║тБ│сђѓ
тюетйЊС╗іуџёТќЄтїќУ»ГтбЃСИГ№╝їС╝»тцДт░╝тЦ│тГљуџёТЋЁС║ІС╗ЇжђџУ┐ЄтљёТаиУЅ║Тю»СйютЊЂтњїуЂхС┐«С╝ау╗ЪСИЇТќГУбФжЄЇТќ░У»ажЄісђѓтюеС╗ЦРђюУђХуеБтЈЌУєЈРђЮСИ║жбўТЮљуџётюБтЃЈућ╗СИГ№╝їтЇЂтГЌТъХСИІУифуЮђуџёТі╣тцДТІЅжЕгтѕЕС║џУ║ФТЌЂ№╝їу╗ЈтИИС╝џућ╗СИіСИђтЈфт░Јт░ЈуџёждЎУєЈуЊХ№╝їСйюСИ║УЙеУ«цтЦ╣уџёУ▒АтЙЂсђѓтюеуј░С╗БТЋгТІюжЪ│С╣љжЄї№╝їсђіAlabaster
JarсђІсђіAlabaster BoxсђІуГЅУ«ИтцџУ»ЌТГї№╝їСИђтєЇтћ▒тЄ║РђюТѕЉУдЂТііТѕЉтЁежЃетђњтюеСИ╗жЮбтЅЇРђЮуџётЉіуЎйсђѓтјєС╗БуЂхС┐«т«ХСИјУ«▓жЂЊУђЁС╣ЪтИИТііждЎУєЈуџёУігУі│№╝їТ»ћСйюС╗јуа┤убјућЪтЉйСИГТхЂТиїтЄ║ТЮЦуџёТЂЕтЁИС╣ІждЎРђћРђћСИЇТў»тюеућЪтЉйт«їТЋ┤ТЌау╝║уџёТЌХтђЎ№╝їУђїТў»тюеујЅуЊХУбФТЅЊубјуџёжѓБСИђтѕ╗№╝їТхЊуЃѕуџёждЎТ░ћТќ╣ТЅЇтЏЏТЋБт╝ђТЮЦсђѓ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уџёУ«▓жЂЊС╣ЪСИјУ┐ЎС╝ау╗ЪС║ДућЪтЁ▒жИБ№╝їтЇ┤тЈѕСИЇУ«ЕУ┐ЎждЎТ░ћтЂюуЋЎтюеТійУ▒АуџёТ»ћтќ╗С╣ІСИГ№╝їУђїТў»Тііт«ЃТћЙтЏътѕ░УђХуеБСИјТѕЉС╗гС╣ІжЌ┤уюЪт«ъуџётЁ│у│╗жЄї№╝їСй┐С╣ІжЄЇТќ░ж▓юТ┤╗сђѓ
тйњТа╣у╗Њт║Ћ№╝їУ┐ЎТ«ху╗ЈТќЄтљЉТѕЉС╗гТ»ЈСИфС║║ТіЏтЄ║тљїСИђСИфжЌ«жбў№╝џтюеУ┐ЎСИфТЋЁС║ІжЄї№╝їТѕЉТЏ┤тЃЈУ░Ђ№╝ЪТў»жѓБСйЇТЅЊуа┤ујЅуЊХсђЂт░єждЎУєЈтђЙтђњтЄ║ТЮЦуџётЦ│тГљ№╝ЪТў»уФЎтюеТЌЂУЙ╣у▓ЙТЅЊу╗єу«ЌсђЂтЪІТђеРђюСИ║СйЋУ┐ЎТаиТхфУ┤╣РђЮуџёжЌетЙњ№╝ЪУ┐ўТў»тюет┐Ѓт║ЋТи▒тцёт»╣уѕ▒уџётю║ТЎ»ТёЪтѕ░СИЇжђѓ№╝їТюђу╗ѕУйгУ║Фуд╗т╝ђСИ╗уџёуі╣тцД№╝Ъ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т╣ХТ▓АТюЅТііУ┐ЎСИфжЌ«жбўтйЊСйюСИђтю║у«ђтЇЋуџёжЂЊтЙиТхІжфї№╝їУђїТў»тйЊСйюСИђС╗йт▒ъуЂхУ»іТќГРђћРђћт«ЃТўЙТўјТѕЉтѕ░т║ЋтюетцџтцДуеІт║дСИіуюЪТГБжбєтЈЌС║єудЈжЪ│№╝їС╣ЪТўЙТўјТѕЉТў»тљдТііУђХуеБуџёуѕ▒№╝їтйЊСйюСИђСИфуюЪт«ътЈЉућЪтюеТѕЉУ║ФСИіуџёС║ІС╗Х№╝їУђїСИЇтЈфТў»ТійУ▒АТЋЎС╣ЅсђѓтдѓТъютЪ║уЮБуџёуѕ▒тДІу╗ѕтЈфтЂюуЋЎтюеУДѓт┐хжЄї№╝їжѓБС╣ѕтѕФС║║уџёуї«У║ФуюІУхиТЮЦТђ╗С╝џУ┐Єтц┤№╝їућџУЄ│ТўЙтЙЌтЇ▒жЎЕсђѓСйєтйЊжѓБтюетЇЂтГЌТъХСИіуѕ▒ТѕЉтѕ░т║Ћуџёуѕ▒№╝їуюЪТГБт╝ђтДІтюеТѕЉжЄїжЮбТЅјТа╣ТЌХ№╝їТѕЉт░▒С╝џТИљТИљТІЦТюЅСИђуДЇРђюТёџТІЎРђЮуџётІЄТ░ћРђћРђћтЂюТГбУ«Ау«Ќ№╝їтІЄТЋбтю░ТЅЊуа┤ТѕЉУЄфти▒уџёујЅуЊХсђѓ
Тюђтљј№╝їУ«▓жЂЊтЈѕтЏътѕ░С║єУхиуѓ╣№╝џУђХуеБУх░У┐Џж║╗жБјуЌЁС║║УЦ┐жЌет«ХуџёжѓБС╗йуѕ▒№╝їТІЦТі▒т╣ХСИ║жѓБуйфС║║тЦ│тГљУЙЕТіцуџёжѓБС╗йуѕ▒№╝їСИђуЏ┤СИ║жЌетЙњС┐ЮуЋЎСйЇуй«сђЂуГЅтђЎС╗ќС╗гуџёжѓБС╗йуѕ▒сђѓУІЦућетєижЮЎуџёую╝тЁЅТЮЦуюІ№╝їСИ╗уџёуѕ▒С╝╝С╣јтцётцёжЃйТў»РђюТхфУ┤╣РђЮ№╝џСИ║т░єУдЂтЄ║тЇќуЦѓуџёжЌетЙњТхЂТ│фуЦѕуЦи№╝їСИ║тЇ│т░єжђЃУиЉуџёС║║уЙцТхЂтЄ║т«ЮУАђ№╝їСИ║С╝џУйгУ║Фуд╗тј╗уџёС║║Уђљт┐ЃуГЅтђЎтѕ░т║ЋсђѓуёХУђї№╝їУІЦСИЇТў»У┐ЎуюІС╝╝ТхфУ┤╣уџёуѕ▒№╝їТѕЉС╗гТа╣ТюгСИЇтЈ»УЃйУ«цУ»єудЈжЪ│сђѓС║јТў»жЌ«жбўУЄфуёХтю░УбФу┐╗УйгУ┐ЄТЮЦ№╝џРђюСИ╗ТЌбуёХСИ║ТѕЉУ┐ЎТаиРђўТхфУ┤╣РђЎ№╝їжѓБТѕЉуЕХуФЪУ┐ўтюеу┤Ду┤ДТіЊСйЈС╗ђС╣ѕСИЇУѓ»ТћЙТЅІтЉб№╝ЪРђЮТў»ТЌХжЌ┤№╝ЪТў»жЄЉжњ▒№╝ЪТў»жЮбтГљтњїт«Ѕуе│уџёТюфТЮЦ№╝ЪС╝»тцДт░╝тЦ│тГљуџёТЋЁС║І№╝їу╗ѕуЕХТў»тюеУ┐йжЌ«ТѕЉС╗г№╝џтљёУЄфТЅІСИГжѓБтЈфујЅуЊХуЕХуФЪТў»С╗ђС╣ѕ№╝ЪтЈѕСйЋТЌХТё┐ТёЈтюеСИ╗жЮбтЅЇТііт«ЃТЅЊубј№╝ЪУ┐ЎТў»СИђСИфт«ЅжЮЎ№╝їтЇ┤ТЌаС╗јтЏъжЂ┐уџёжѓђУ»исђѓ
УђХуеБТЏЙУ»┤№╝џРђюТѕЉт«ътюетЉіУ»ЅСйаС╗г№╝їТЎ«тцЕС╣ІСИІ№╝їТЌаУ«║тюеС╗ђС╣ѕтю░Тќ╣С╝аУ┐ЎудЈжЪ│№╝їС╣ЪУдЂУ┐░У»┤У┐ЎтЦ│С║║ТЅђУАїуџё№╝їС╗ЦСИ║У«░т┐хсђѓРђЮУ┐Ўт║ћУ«И№╝їС╗ітцЕС╗ЇтюеТѕљт░▒РђћРђћтђЪуЮђтЃЈт╝атцДтЇФуЅДтИѕУ┐ЎТаиуџёУ«▓жЂЊУђЁуџётЈБ№╝їС╣ЪтђЪуЮђТ»ЈСИђСйЇУ»╗тѕ░У┐Ўу»ЄТќЄтГЌС╣ІС║║уџёућЪтЉйУђїТѕљт░▒сђѓжѓБждЎУєЈуџёУігУі│ТЌЕти▓тЁЁТ╗АС╝»тцДт░╝УЦ┐жЌеуџёт«Х№╝їтдѓС╗іТГБуГЅуЮђтЁЁТ╗АТѕЉС╗гуџёТЌЦтИИСИјтЁ│у│╗сђЂТЋгТІюСИјуї«У║ФсђѓжѓБС║ЏСИЇТііуѕ▒тЈФСйюТхфУ┤╣№╝їтЈЇтђњТгбтќюжђЅТІЕРђюТхфУ┤╣РђЮуџёС║║№╝їУЂџтюеСИђУхиуџётю░Тќ╣№╝їТЅЇТў»уюЪТГБуџёТЋЎС╝џ№╝ЏУђїС╗ќС╗гуџёућЪтЉйТюгУ║Ф№╝їТГБТў»тљЉСИќуЋїТЅђт▒Ћуц║уџёсђЂТюђТюЅУ»┤ТюЇтіЏуџёудЈжЪ│УДЂУ»Ђсђѓ